周月峰(罗志田|从“复杂和多歧的现象”中呈现新文化运动)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周月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即将出版,264页,78.00元
周月峰的书《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要出版了,他给我以写序的荣幸,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月峰本科和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2005年曾到北京大学旁听过我的课,之后提出要跟我念博士,并于次年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在我的学生中,月峰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身有残疾,小时遭高压电击,失去双手。按照当年上面的规定,对于这样身体状况的考生,学校是可以拒收的。幸运的是当年北大历史学系的牛大勇主任和研究生院都极有同情心,一再打破“条条框框”,破格把他录取进来。此后月峰即在我指导下读书,到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本书即是据他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学生和老师
最近一二十年是一个学术见解纷歧的时代,各大学在研究生阶段的教与学,常有较大的不同。例如所谓“新史学”,不同的人,理解可能相去甚远(如我们现在至少有两种《新史学》集刊,其所揭出的“新史学”,最多也就是异曲同工而已)。记得北大历史学系好几位要跟我做“新史学”的学生,我都劝他们另找更合适的老师。这可能让他们失望,但他们想要做的那种“新史学”,若让我指导确实感觉力有不逮(这不是假客气。正常情况下,学生试图进入的领域,是需要老师去学习的,我也很愿意这么做。不过我感觉他们心有所向的选择已较为固化,不是我在短时间内可以跟得上的)。
我不是那种守旧而“冬烘”的老师,也曾试图跟上史学的更新。记得当年戴维斯(Natalie Z. Davis)那本《马丁·盖尔归来》在美国曾有过争议,我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也曾把那本书和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两篇重要的争论文章发给大家讨论,结果几乎所有人都在争论归来的马丁·盖尔究竟是真是假,而我想引起大家关注的,却是当时美国史学一些发展中的走向。
用戴维斯的概括说,她的批评者芬莱(Robert Finlay)是“以简单明晰的线条来看待事物;他希望得到绝对的真相,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辞建立起来的真相,没有任何含混模棱之意”;而戴维斯自己则“处处看见复杂和多歧的现象;在继续寻求更确切的知识和真相时”,也“愿意先接受推想出来的知识和可能得出的真相”。
这是我特别想让同学们关注的核心观念,以知晓在那时的美国也存在至少两种研究取向,一是较为传统的,追求黑白分明的绝对真相,并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辞表述出来;一是相对新兴的,注意到历史上复杂和多歧的现象,愿意接受这样的历史“现实”,并在表述中呈现这样的历史。类似的分歧在中国史学界也存在,似乎接近芬莱取向的人更多一些,但我总希望我们的史学能更多展示历史的丰富性。
现在博士生教育的一个现实是,学生多为武林所谓“带艺投师”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师生之间的“磨合”并不容易,有时甚至可能是痛苦的(出现这样的情形主要是老师的责任)。最理想的结果是杜甫所谓“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为己有。月峰在浙江大学所受的史学教育,风格与我在北大的教法颇有不同,所以他读得并不轻松。且由于我不善引导,中间也曾有困顿的时候,还好没影响他继续努力。我一向建议学生扬长避短,所以鼓励他在坚守浙大史学优点的基础上试着往新的取向转。到毕业时,月峰有了显著的转变,我在邮件中说他“真是脱胎换骨”。然而所脱所换,不过是外在的表象。借用柯林武德的话说,若以此前的状态为P1,后来的结果为P2,此前的“P1从未终止,它转变为P2的形式继续前行”。从月峰后来论述的一招一式中,都可以窥见浙大史学的风范。
从博士论文到专著
我在和月峰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希望他能选择资料相对集中、不必四处奔波搜集史料的选题。月峰说他感兴趣的是近代精英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他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有关晚年梁启超的研究。我那时曾让面临学位论文要求的学生每两周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梳理既存的相关研究并说出自己论文可能做出的贡献。记得月峰所提的选题有太平天国运动后的书籍印刷与阅读、近代的俄国形象、太虚与佛化运动、“梁启超系”与新文化运动等。根据月峰的研究基础和个人意愿,我建议他考虑最后那个选题,并得到他的同意。
月峰在读书期间学习非常努力,曾以两年时间系统阅读了五四前后数年的《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晨报》《民国日报》《公言报》等报纸,形成了对此一时期思想界的整体认知。又进而细致研读“梁启超系”所办的《大中华》《解放与改造》,以及其他群体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建设》《星期评论》等期刊和各类时人文集,对各方思虑有了较为周全的把握。
其实“梁启超系”本身是个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称谓。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派”或“系”,如一般常说的“研究系”,是当时人的用语,可以说是确有那么一个“系”存在。但“研究系”侧重政治,与文化有些偏离,用来说文化运动显得不甚合适。而在梁启超欧游期间及回国后,确有那么一些在相当程度上感觉志同道合的学人围绕在他身边,如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张东荪、蓝公武等,并有不少共同的努力。但这只是一个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松散群体,界定为一个“派”或“系”,或有些牵强。我们也曾反复斟酌,好像没有更合适的称谓,所以在不那么“绝对”的基础上,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暂时这么用着。
在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就梁启超一生而言,戊戌前后或是最显“进步”的时刻,其次是护国运动时期,五四前后已是被认为“落伍”的一段。相较于胡适、陈独秀等人,五四前后的梁启超在时人眼中的确不那么“进步”。其实他这样的思想大家在那时不仅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颇为活跃,只是在我们既存研究中对其关注不足而已。

梁启超,1917年。
说到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百多年来许多人为它树碑立传,其形象确更清晰,却也依然如雾中之月,微茫而朦胧,尤其对运动的丰富性明显表现不足,大有深入探索的余地。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面相来表述全体,在中外学界都很流行。既存研究便多以《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的声音来概括整个新文化运动,而忽视其复调的一面。这一倾向具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群体很早就确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正统”地位。“正统”地位的确立明显影响了史家的取舍,多少导致了对其他努力的遮蔽。其实当时试图从文化层面来改变中国现状的有意努力尚多,“梁启超系”就是其中最为活跃也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再现他们的言行及其背后的思虑,更能展示运动的丰富面相。
“梁启超系”在五四前后的多方文化努力,长期被后人忽视。能将其梳理出来,就是个不小贡献。月峰的博士论文做到了这一点,让读者看到了“梁启超系”当时在文化上的积极进取。博士论文完成后,他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走入当时思想世界,进一步呈现出“梁启超系”的新文化努力与其他类似努力的关联互动,对认识新文化运动有多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修改后的书稿,更加深入周详,是前后努力的结晶。
张君劢后来曾借纪念蒋百里的机会,实际概括了“梁启超系”在五四前后的事业,他说:
民国八年,公(蒋百里)归自欧西,携《欧洲文艺复兴史稿》以返,与五四运动作桴鼓应。同时主持共学社,印行有关文艺与学术之书数十种。又尝办讲学社,杜威、罗素、杜里舒、太戈尔之东来,皆出于公与新会先生之罗致。呜呼,公为军人,而有造于近年新思潮之发展者如是。
说的是蒋百里个人,其实表出了群体的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感觉到世界文化的转变,梁启超个人的努力重心由政治活动转入思想学术,围绕在他周围那些年轻一辈的学人,对此尤为积极,颇思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在文化上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张君劢提到的“共学社”,就是这一文化努力的核心机构。
毋庸置疑,“梁启超系”的文化努力在一些基本面相上与已获新文化“正统”地位的《新青年》群体是有差别的,后者以“民主”与“科学”为号召,而前者以“解放”和“改造”为中心。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思想特别解放,而“梁启超系”的文化运动也特别凸显“解放”的一面。张东荪在五四学生运动后就曾宣称“当首先从事于解放”,且“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 此后梁启超更强调“思想解放”需要“彻底”,要“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尽管他们内部对“解放”的认识和取向也有不同,但他们对“解放”的强调更多是主动的追求,包含着对既存政权与制度的“解放”,可以说相当彻底。
简言之,梁启超等人有其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之所以进入群体性的文化运动,既是看到了世界转变的时代机遇和中国的需要,也不无眼见众多知识青年纷纷投入《新青年》群体麾下而思争取之意。但整体言,“梁启超系”的文化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赞成或反对,也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团体影响,更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的责任心。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他是要“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这应当可以代表整个“梁启超系”的文化构想。近年一些注意到“梁启超系”的研究,多从赞成或反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一面着眼,以白话文学、反传统等“正统”标准来衡量、定义他们,或许忽视了他们真正的关怀。
上引张君劢的文字写于1938年,所谓“与五四运动作桴鼓应”,既有时过境迁之后不再思与“正统”竞争之意,却也是一种实述。“梁启超系”介入了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论争,包括戏剧改良讨论、新旧思想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论争、社会主义论战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正是这些努力和论争,影响甚至形塑了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可以说是“作桴鼓应”。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系”的言说看作他们为“新思想界缔造开国规模”的行动,不仅可以重新理解他们的言论、著述——如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蒋百里之《欧洲文艺复兴史》,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诠释他们所参与的上述思想论争及其他重大思想文化事件,赋予旧论题以新思路,或可产生更多的新研究成绩。
呈现一个更丰富的新文化运动
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月峰的研究似比较亲近前引戴维斯所说的新史学取向。不论是博士论文还是现在成型的书,都试图从各种“复杂和多歧的现象”中呈现新文化运动那丰富的一面。同时他也并不追求所谓“全面系统”,如曾跟随梁启超游欧并担任共学社干事的丁文江,就很少被提及(这可能与材料相对少有关,《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了解“梁启超系”文化活动的重要资源,而承担为梁启超修谱重任的丁文江,有意无意间在年谱中较少提到自己,这可能是丁文江主动“置身事外”的渊源。听说月峰会专门写一篇与丁文江相关的文章)。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曾说,任何“体系”通常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要求一致的结构,要有秩序地组织和表达思想,也就压抑着客体自身各方面的内在统一性。同时,客体间彼此具有的密切联系,也因对秩序的“科学”需要而成为禁忌。即使对于不可免的矛盾,也不能不“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阿多诺自己以“反体系”著称,但他的确看到了体系构建的问题所在。
一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大致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而不论广义狭义,五四运动都不是一个真正自足的体系。它本身并非谋定而后动,而是许多想得不一样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创造历史,在发展中完型,成为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这一运动当然有其不约而同、众皆呼应的主题,然也确实头绪纷纭,始终具有开放性。若将其以某些后设的主题重新组织,以维持整体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或隐含着不小的危险。
盖若有意识地去构建系统性,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在历史人物的前后行为间建立起一种可能本不存在的一致性。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就曾批评某些经典解释者在工作进行之前,便赋予某个经典作家或经典文本的思想以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其结果,即使在文本中遇到了不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内容,也要想方设法利用后设的主题将文本重新组织,以维持其整体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此即他所谓“一致性迷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任何归纳都是一种简化,事物和语言的丰富性会因此而部分失落甚至湮没。
月峰这本书在梳理“梁启超系”的文化方案时,基本做到了放弃所谓系统的先入之见,不以中国传统或近代西方的观念体系为预设标准来衡量,直接进入他们相对直观的思想世界。本书并未分门别类地总结“梁启超系”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未定性他们是复古抑或西化,而是透过表象,将他们此一时期的言论、事业视为改造社会国家的具体行动,呈现出其文化方案所蕴含的意图、他们对现实社会改造问题的介入,及其文化努力在当时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光谱中的位置。
从史学看,言即是行。月峰在本书绪论中说:“相对于偏向抽象思想的、静态的思想史研究,本书更倾向于勾勒五四思想界动态的‘肌理’(sinews)。”这是一个有抱负的尝试。陈垣在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后曾说自己“着眼处不在佛教”,因为“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或许月峰也希望不就“梁启超系”言“梁启超系”,而使凡欲了解五四者“不可不一读”此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是一个复调的运动,其内部不同的声音既各自独立,又共同参与并形塑出一个更大的和声。变化的史事需要发展的理解,丰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表述。故叙述那段历史,既要表现出时代的“公言”,也当再现各种独特的“私言”,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史事。
本书便是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新文化运动。书名虽为“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但作者的眼界并不局限于“梁启超系”他们的“另一场”,而是随处可见《新青年》及北大师生为主的人和事,以及国民党人的言行,使多方都进入整体图景。全书将新文化运动视作完成中的“现在进行时”,以动态的图像取代过去偏向静态的研究,使各方话题的汇聚与转移、态度的冲突与缓和、观念的竞争与妥协,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构成因素。故再现“梁启超系”文化运动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在一种声音之外加入了另一种的声音,而是呈现他们参与时代思考、形塑时代声音的过程,在关联互动中呈现一个比过去的认知远更丰富的新文化运动。
我在多年前曾主张思想史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并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本书便不仅能让读者看到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这些思想者怎样思想,更让读者看到五四思想界如何生成的历史进程。换言之,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呈现新文化运动静态的“骨骼”与“血肉”,而是更进一层,在过程中展现新文化运动动态生成的“肌理”。可以说本书不仅填补了既存研究的空白,并且拓宽了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胡适一生曾多次引用“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这句话。我愿意借这一句式说:现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出版了,以后要论述新文化运动,恐怕需要有所修改了。
- 主持人走光(北京这一夜,陈数摔倒走光,闰妮风情万种,主持人翻车陈凯歌不满)
- 张苏军(副区长等4人当“保护伞”被查后,区政协主席也落马了)
- 加油站卖烟吗(加油站抽根烟会咋样?)
- 挂靠单位交社保(挂靠企业缴纳社保有什么优缺点?和灵活就业相比哪个性价比更高?)
- 京东商家登录(京东商家助手使用方法介绍 网络设置对话框功能说明)
- 济南市统计局(聚焦“项目突破年”济南市统计局将加强对十大领域重点项目开工及建设进度情况监测)
- 陈庆云(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庆云逝世系我国有机氟化学开拓者)
- 杨舒越(cba啦啦队哪个最漂亮?篮球宝贝颜值排行)
- 上海家化(龙头易主,上海家化失去的四年)
- 四平日报(2017,四平日报在做啥?)
- 王命旗牌(说一说清朝的“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
- hwm(详解oracle中move的执行机制+通过move操作来降低HWM大小)
-

主持人走光(北京这一夜,陈数摔倒走光,闰妮风情万种,主持人翻车陈凯歌不满)
2015.12.16 -

张苏军(副区长等4人当“保护伞”被查后,区政协主席也落马了)
2015.12.16 -

加油站卖烟吗(加油站抽根烟会咋样?)
2015.12.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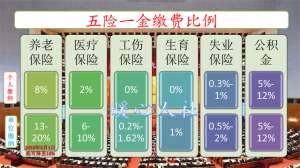
挂靠单位交社保(挂靠企业缴纳社保有什么优缺点?和灵活就业相比哪个性价比更高?)
2015.12.16